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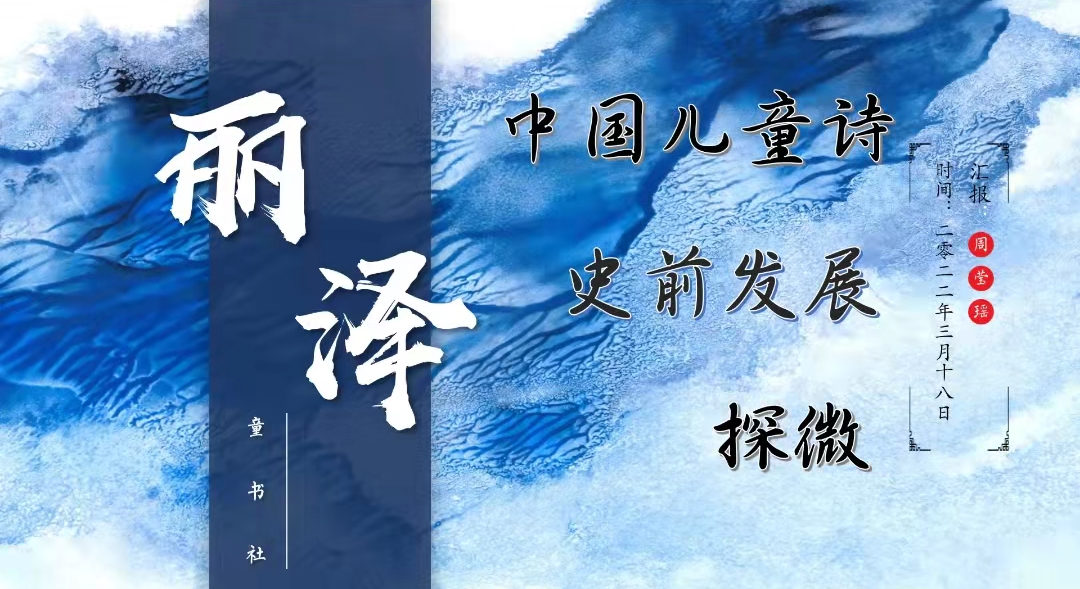
近日,丽泽童书社邀请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博士生周莹瑶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中国儿童诗史前期发展微探”的线上讲座,本场讲座由浙师大儿童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翔宇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主持人吴翔宇教授便提到,对于史前期的整个中国儿童文学,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材料并不多,其关注者也不多,直到“五四”时期及之后,儿童文学才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并逐步发展的局面,因此史前期的儿童文学是比较薄弱的。薄弱并不意味着史前期的儿童诗及儿童文学没有研究的价值。主讲嘉宾周莹瑶首先为大家厘清了两个概念,即“史前期的界定”及“儿童诗的定义”,接着她从“古代童谣:徒歌谓之谣”“儿歌的出现”“未曾自觉的儿童诗”“近代儿童诗的发生”等四个方面来进行分享。
在“古代童谣”方面,周莹瑶先从童谣的定义、起源及其预言性质等方面来介绍,古代的童谣资源是很丰富的,如《后汉书》中就记载了不少的童谣作品。讲座过程中,同学们纷纷回忆起了自己印象中的古代童谣,如“五月五是端午”等关于传统节日的一些童谣。乱世时的童谣有一定的舆论导向作用,因为其口语化与民间化,易于宣传政治理想。但南宋后市民阶级兴起,很多童谣开始脱离政治,变得更加的儿童化与生活化,累积了不少民间文学资源。
在“儿歌的出现”方面,周莹瑶从儿歌的定义及明代的一些儿歌集的介绍入手,为我们阐明了古代儿歌的发展。儿歌其实与童谣并无区别,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将较民间化的称为童谣,较文人化的称为儿歌,这种指认也有一定的合理性。明代吕得胜的《小儿语》是一部供给孩子们阅读并益于修身养性的蒙书,以格言式的语言呈现,被称为“天籁”。而其子吕坤续写的《续小儿语》则教化色彩更浓郁,也被称为“人籁”。吕坤还编著了一本《演小儿语》,其以歌谣的形式传达了对儿童的教育思想,脱离了格言的格式,使用了更加口语化的自由形式,更适合儿童的欣赏。明清时期还出现《天籁集》《广天籁集》等儿歌集子。
在“未曾自觉的儿童诗”方面,周莹瑶主要介绍了一些蒙学诗歌读本及文人创作的儿童题材诗歌。文人创作的有《小儿垂钓》《古朗月行》《开孙满月》等儿童题材的诗作。蒙学诗歌读本像我们熟知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都是用韵文写作的,它们在严格意义上并非诗歌,但对儿童有韵律上的启蒙。像《笠翁对韵》《声律启蒙》等也有助于儿童认识诗歌形式、认识语言等,也可称为准蒙学诗歌读本。而《千家诗》也是重要的儿童诗歌教材,类似百科全书与博物志,其按照天空、月亮等题材分类来罗列诗歌,使孩子们便于仿写,有助于教导训练孩子的写作。另外,她还提及了一些古代的儿童作诗现象,如王勃、骆宾王、汪洙等。儿童自己的写作是儿童诗教的反馈,也是诗歌与儿童双向互动的一种呈现方式。
在“近代儿童诗的诞生”方面,周莹瑶提到,晚清的政治变革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如梁启超发起的“诗界革命”,即强调以古文写出新意境,他也写下了一些爱国诗歌,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儿童诗。而黄遵宪是晚清儿童诗的代表,写下了不少真正的儿童诗,如《幼稚园上学歌》等。而“新童谣”则是以童谣为载体的一场启蒙思想的传播运动,先人发现童谣可以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晚清的报刊开辟了很多关于“新童谣”的栏目,如杭州的《白话报》,其刊登了许多时政批评的童谣。歌谣体有利于口耳相传,把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传播到民间,同时也促进了童谣形式的变革,其内容慢慢转向描写现代的生活与思想。她还介绍了当时童诗的一种音乐性试探——学堂乐歌,因为学校歌唱科目的开设需要,中国的音乐家们纷纷将外国的音乐旋律与中国的诗歌相结合,创作了不少学堂乐歌,这可以被视为中国近代儿歌的先声,较有名的如李叔同的《送别》。此外,儿童游戏诗也是儿童诗的一种重要类型。五四之前,白话儿童诗诞生了,如周作人在1914年发表的《儿歌》即为典型的白话儿童诗。
最后,周莹瑶总结道,在中国古代,儿童诗长期存在,民间流传的童谣成为儿童诗的重要部分;与此同时文人将其自觉地编写为儿歌,文人也创作了不少以儿童为对象的作品,主要存在于蒙学读物中;晚清随着启蒙思想的传播,诗歌成为了召唤民族觉醒的载体,促成了中国近代儿童诗的发生。
(丽泽童书社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