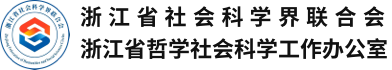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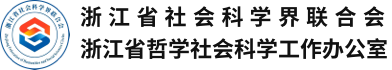
1956年春,浙江省教育厅为加急培养一批中学教师,从全省中等师范应届毕业班中选拔一批学生,提前报送至浙江师范学院接受大专教育,缘此,我有幸入学浙师院中文科。那时,学校对我们这批包送生非常重视,在校的著名学者,例如姜亮夫、夏承焘、王驾吾、任铭然、孙席珍、吕漠野等先生都无例外地给我们上过课,为我打开了知识宝库的大门,教给了在知识海洋中探宝的基本技能,激发起追求知识的的强烈愿望。师长们的学识和治学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诱发我决心在当好一名语文教师的同时,树立了“希望在求知上有所建树”的志向。
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寻找一条合适的求知之路并不容易。但我几经波折还是找到了,现先将我的寻觅经历和所得教训,略述如下:
开始认真做所谓的学问是在1962年。那时我已在中学执教整整五年,自觉对语文教学已得心应手,而学术界的形势又有了新变化,我那深藏于心的“希望在求知上有所建树”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我选择“形象思维”作为研究对象,开始研究的准备。我只受过内容简浅的专科教育,没有完整、专业的学术训练,而我所选的研究题目又与原来所学风马牛不相及。因此我必须从零开始。我化力气补学专业教材、调整订阅书刊、多途径了解研究现状、大量摘录资料卡片,按着老师们教我的方法,中规中矩地开始做起学问来。四年之后,觉得稍有了点底气,就想试试刀了。当时,我国形象思维研究上的权威是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方名教授,正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文章。我就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王老的论文提出我的看法,同时写出我的研究计划,请王老指导。想不到这信得到了他的热情鼓励,被称为“来自东南沿海的空谷足音”,当时的高兴劲,现在想起来还很激动。但正当我满怀信心准备大干一场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王方名教授不久就上了《人民日报》,成为需批倒批臭,还要踏上一只脚的“反动学术权威”。于是我诚惶诚恐地烧毁了与王老的通信、大量的笔记和卡片……彻底收手。
这次挫折给我很大的打击,甚至一度决心要由文转理,走另一条人生的道路。我主动请缨去校办工厂:始而读中医、中药书,上山采中草药;继而学电子技术,用视波管组装电视接收机,并研究设计当时国内还没有的电子琴,其成果还被列为浙江省四新产品。但其实,深埋我心中的梦想并未泯灭。到了拨乱反正的新时期,大批知识分子若久旱逢甘霖般重新走上了求知之路。对此我曾犹豫观望了很长时间。直到1982年,形势是越来越好,深藏于心底的愿望遂又苏醒过来。其时,我已回到中文教学专业,我就以语文教学中常常碰到的“存活在现代汉语中的古汉语成分”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回答古人语言中怎样的东西才是有生命力的?如何充分合理地利用它们?选择时有哪些科学标准?活古语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些什么作用?如何防止或纠正活古语使用中的不良倾向?古语活用有没有规律性的东西应加以总结?活古语研究与现代汉语教学有什么关系等等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显著的现实价值。为此我列出了十余个分支题目,开始了切实的学习和探索。研究很快取得了进展,陆续发表了《“活”古语的研究与教学》《试论“活”古语的修辞功能》《成语与古汉语》等论文,教学工作也有了新的提高。但不久,我奉调到慈溪县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在新岗位的千头万绪中,这项我中意的研究又被搁置了下来。
两次投身学术研究的对比,促使我对20余年来走过的道路进行反思,以便更好地在新岗位上继续我的求知之路。在反思中我将早年发表的文字编成《蹒跚二十年集》出版,成为我求知路上的一个阶段性小结。
反思的结果,确定了我对自己求知之路,拟定一些约束和期许。我认为像我这样的智力平平,又工作在非专业研究机构的最基层人员,求知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必妄自菲薄,要将自己的求知活动与岗位工作妥善地结合起来,严格把握住几个方面。
一是像我这样没有受过正规治学训练的普通知识分子,须先找个小课题,按照人文科学的研究常规进行一次完整的治学实习,以便领会《学人谈治学》之类书籍中谆谆教诲的真知隽言,为自己的求知活动打下坚实的方法论基础和良好的治学品格。我当年选学形象思维当然很不明智,但我并不懊悔走过那一段弯路。因为那是我用自学的方式经历的一次治学实习,对我一生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二是要把本职工作看成一座易“得月”的“近水楼台”,在其中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这是工作在非专业研究机构,又有强烈研究欲望的人们比较现实的可行之路。因为这样的课题,一方面由于来自现实需要,能切实地服务社会,又由于来自相关学科的活水源头,易于从中发现新视角、衍生新观念,利于理论的创新;另一方面,研究成果能给本职工作提供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利于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总之,这是一条能使岗位工作和研究工作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求知之路。
三是要防止好高骛远,不要试图全面深入某学科,以免陷入另一类的“两股道上跑车”的困境。这种撰写专著的诱惑是常会发生的,譬如我曾在一家学报上发表《浙东食俗与饮食文化的思考》,事后就有出版社来函,约我写一本关于浙东食俗的专著。当时我写那篇论文,目的仅在于更好地了解本地食俗的社会学意义,以便在修志中更好地处理民俗资料;当然同时也有给饮食文化研究者提建议的用意,希望有助于该领域研究的发展。但如果我经不住诱惑,贸然进入并没有全面准备的民俗学领域,结果以我的能力和知识水平,很可能发生研究和岗位工作两败俱伤的局面。
四是对自己进行的那些零散、随机的研究成果也不必妄自菲薄。如果不以成名成家为追求目标,这类研究还是很有意义的。对修志人来说,这类研究能帮助我们对所涉材料作出最妥帖的编辑处理;对相应的学科也会有启发参考、缺漏补遗的作用。何况地方志工作者接触的多是第一手资料,他们对这源头活水的感悟和解读,往往是很鲜活、很真切的,有时还能提供新的视角,暗含着深刻的意蕴;有象牙塔中学人所没有的优势。
此后近30年,我就在修志岗位上按照自己选定的求知道路摸索前行,参与了8部不同类型的地方志编纂,又在方志理论和地域文化研究上取得了些许成果。
窗体底端
进地方志办公室以前,我曾担任多届慈溪县作家协会主席,对三北地区的地方文化多有接触;而地方志又是我从事教育研究的一种参考资料,我“文革”后重新写作的首篇论文《乡土教育与思想工作》,就引用了大量方志资料。因此,新的工作岗位对我是有吸引力的。只不过于方志编纂却是门外汉。因此,我的自我培训还是花了约两年时间。主要是阅读权威论著和参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地方志学科性质的大讨论。地方志是历史学和地理学间的交叉学科,对于我陌生的地理学和地图学,还在陈桥驿先生的热心指导下进行了“恶补”。此后,我就一方面投入地方志编修工作,一方面选定“地方志编撰如何科学化、现代化”和“新方志如何进一步改革创新”两个课题开展研究,先后发表了近30篇论文,出版了《秋斋聊志》《中国图志的继承和创新》两本专著。在研究中,我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要求,或者在论文发表后即加以应用,或者先在修志中试用后再撰文作理论总结。这让我得益匪浅,我参与编纂的8部方志类作品能有3部在国家级评选活动中先后获奖,大约和这些研究不无关系。
一、关于地方志编纂的科学化和现代化
我对如何提高现代地方志书质量提出了一些看法,并努力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其中主要有:
(一)我认为争取专家参与是提高新编地方志质量的保证。这在我的《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为了无愧于社会主义新方志》和《慈溪县志编纂始末》《漫谈志稿的评后深加工》等文中都有所探讨。但在现实中要实现专家主持修志几乎没有可能,联系实际时就退而求其次,千方百计地争取专家参与志稿评审,以弥补没有专家直接参与的缺陷。对于《慈溪县志》的评审,除请杭州大学陈桥驿、浙江农业大学胡德芬、上海社科院郑祖安等各学科专家参加评审会外,还函请著名学者陈训慈、史州审看人物稿,吴耕民、史州审看农业稿,陈桥驿、舒绍虎审看自然环境稿和全套地图,,吕以春审看建置稿,复旦大学、华东水利学院、钱塘江工程指挥部专家审看三北平原成陆稿,傅国通审看方言稿,孔凡生审看水利稿,陈桥驿审看盐业稿,夏衍、傅振伦提供相关资料等等。而专家们也多尽心尽力,如陈训慈在人物稿上的批注就多达280余处,并撰文作归纳;吴耕民在农业稿上的批注多达234处;史州的读建置、农业、人物稿摘记有2万余字,他们的意见对保证志稿质量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地方志的数据处理,要努力引进现代处理手段。对此,我在《谈方志编纂中资料的整理和加工》《关于现代逻辑在方志编纂中的应用问题》中有所讨论,并在实践中加以应用。例如在人口统计中,我们采用生命表法技术编制出一个年份的“节略生命表”。它篇幅很小,但利用它不仅可用以研究人口的死亡变化,还可广泛地应用于公共卫生、社会保险以及长寿、生育力、人口迁移、人口增长、人口预测以致不同人群寿命的研究,实用中还可以省去每年统计实际人口年龄分布和年龄别死亡率的繁复工作。在方言志材料的选择中,我们参考萨丕尔的“语言有个底座”的观点,选入了语言的历史地域变化资料,真实地反映了本地方言的流变根源。再譬如对自然灾害数据的处理,也依据时间等级序列原理,归纳出宏观的描述。另外,还撰文强调现代逻辑知识的应用等等。所有这些研究和实践,对提高地方志书品位有一定作用。
(三)地图在地方志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要力争多样化、现代化、规范化。地图是地表事物图形化的、可精确计量的载体。通过地图可表达有关物象的空间结构与时间过程,可计量各种关系的数值,可统计各种变量及其变化规律,通过相应要素的对比还可认知各物象的演变和发展,是一种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表述方式。地方志应根据不同内容的需要采用不同的图型,力求多样化;入志地图必须符合现代地图的制作规范,做到地图要素齐全、注记详明。《慈溪县志》所配的地图基本上实现了这个要求。陈桥驿先生曾对自然环境部分的地图做过评价,说“图中内容的丰富,注记符号的详明,都证明了作者的水平”。另外,方志地图出版时还必须标明由国家测绘与地理信息管理部门核发的准予公开出版的地图审核号,说明所有地图已经过保密处理和技术审查,可合法出版。这些意见和相关经验,在我的《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和《再论方志地图的特征及其制作》中有详细的讨论。
(四)在地方志编纂中大力推广数字技术的应用。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让我对海量的地方志资料的应用前景大为乐观,坚信这些汗牛充栋的资料将因此而大放光彩。为此我在一位搞计算机技术的学生的帮助下,学习了计算机的基础知识,开始探索数字化技术在地方志领域的应用,有如下几方面的成果。
1.在对地方志文献和数字化技术有所了解的基础上,发表了《关于地方志出版媒介的革新》和《中国类书的特色与方志文献数据库的开发》等论文,倡议在全国开展地方志资源数字化工作,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同时创建《中国地方志资料库》网站,提倡地方志互联网应用,又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大地研究所开发《古今图书集成电子版》的策划,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古今图书集成>电子版检索方案》供他们参考。
2.从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购买、收集地方志的电子版,至今收集总量已达599.08G,数量庞大且多为扫描本,为我多年来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现在,已将它们交给中共慈溪党史馆,由他们建立地方志文献数据库,为读者服务。
3.策划、开发了一批多功能多媒体地方志读物,它们不是方志文本数据的简单拷贝,而是含视频、音频、图片、文字的展示、检索、提取功能的多媒体作品。计有《浙江省名村志·东阳市志》《浙江新编县 ( 市 ) 志资料集萃》《绍兴县志》《杭州年鉴(1994 — 1999 合订本)》《中国民间艺术品大观(江浙沪卷)》等8种。其中《浙江省名村志·东阳市志》是我国第一张地方志光盘,其盘面图像还出现在地方志成果展览纪念封上。
4.应用计算机技术于地方志大型索引的编制。新编《绍兴县志》是一部篇幅巨大的志书,我得悉他们将编制大型索引很是兴奋,就带领了几位计算机程序员前往了解。那时,他们在打印稿基础上手工制作条目卡片的工作已近尾声,后续工作将十分繁复。经双方认真研究,认为如果此时能引入诸如“中文全文检索系统”“电子文本格式的转换工具”“Windows 下宏录制工具”等计算机文字处理工具,再根据需要开发几种小软件,就能用计算机技术加快工作进程。于是商定安排程序员参与他们的工作,以计算机为辅助工具,高效高质完成索引编制任务。事后,我还在《谈谈地方志索引的编制》一文中谈到了此次实践的相关经验。
二、关于新方志的革新
自1980年代以来,新方志编纂取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但我们不能安于现状,应努力从实践中发现问题,不断改革创新,以进一步提高地方志的学术品位,更好地为现实服务。我在《新编方志面临的几个问题》《新方志编纂中亟待关注的几个问题》等文以及在《秋斋聊志》《慈溪地方志研究》《新编慈溪市图志》的序文或前言中,都有繁简不一的探讨。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有如下5个方面。
(一)、方志学的学科定位需要重新加以讨论。我认为方志学和历史地理学一样,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一个交叉学科,而且是中国特有的。它们两者渊源相似但分野明显,从这个角度开展学科建设既名正言顺又让人耳目一新。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志属信史”论的影响,虽口头上也承认地方志与地理学的关系,承认历史上大量的地志是重要的地方志著作,实际上却将地志边缘化了。方志史上那么重要的一种类型,在如此大规模的编修工作中,几乎看不到与之相承继的作品。在如此的氛围下,方志学必然成为史学的一个分支,根本就独立不出来。现在应是重新讨论地方志学科定位的时候了。
(二)、要继承发扬地方志多样化的传统。地方志本来就有多样化的传统,有类似综合史料集的一般地方志,有以地理资料为主的地志,还有特别重视图像的图经和图志等等。上面已提到,目前有刻意淡化地志类方志的趋向。事实上,地志在历史上恰恰是最早出现的,最先建立相关管理机构的、最早出现全国总志的一种类型,在近代又是最先实现了现代化转型的方志类型(可以《中国分省地志》丛书为例),被边缘化实在很可惜。为了提倡方志的多样化,我自知编纂地志的可能性很小,于是转而从事图志的编纂。先后编纂出版了《慈溪市图志》及其续志《新编慈溪市图志》,还出版了仿效专业图志的《慈溪文化鸟瞰》,还编纂出版相关的快餐式图件《中日韩徐福传承地分布图》《慈溪市文化地图》,形成了一个系列,开始引起方志界的关注,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赞赏,编纂情况被列入《中国方志五十年史事录》,《浙江方志》还辟专栏予以评介。《新编慈溪市图志》出版后我还主编出版了《中国图志的继承和创新》论文集,介绍了图志研究成果。
(三)、地方志的内容及服务对象须随文化背景的变化加以调整。历代地方志与新方志编纂的文化背景有巨大的差别。新方志所处的时代,已形成细分的学科体系,各学科大都已有完备的资料检测、收集、整理、存聚的机构和规制。这使新编地方志提供的资料不能像旧方志那样被读者视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而只能是专业资料的简化和摘编,是一批被非专业编辑改造了的二手材料。因此,新方志推广中出现“专业人员不想看,普通读者看不懂”的尴尬局面实在非常自然。我想现在应该重新定位新方志的内容、规模和服务对象,不能简单地套用我们对旧方志的认识。
(四)、志稿评审存在轻内容重形式的趋向,影响了评审质量。我长期关注各地的新志评审,发现各科专家参与的几率似乎在渐渐减少,有的地方简直只邀请编志机构领导和所谓方志专家参加。这种情况非常让人担忧,我在《秋斋聊志》的自序中以及《对志稿评审工作的三点建议》文中指出:如果只请清一色的地方志专家评审,极易产生重形式轻内容的倾向,严重时甚至会导致方志新八股的产生,这绝不是什么杞人忧天。
(五)、“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和“溢美乡里”的旧方志弊端,仍时有所见,仍须注意克服。这一点其实大家都明白,问题是如何克服。
我一直认为,地方志工作者在完成编志任务外,应主动利用编志中收集到的丰富地情资料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并以其成果为本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服务,绝不可编完志书就刀枪入库、放马南山!我30余年在这方面的坚持也取得些许成果,后来多收在《寻绎慈溪文化之源流》和《秋斋论丛(上、下册)》中。现举例作简单介绍。
一是深入研究当地特色历史文化,扩大其对外影响。例如上林湖越窑青瓷是慈溪首屈一指的文化遗存,对慈溪发展有极为深刻的影响。我曾就陶瓷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关系开展研究,撰成《从陶瓷文化看中国海洋文化的若干特征》一文,发表在《浙江海洋学院学报》,同时收入《中国海洋学会2007年学术年会论文集》,并被中国海洋学会评为优秀论文。我曾应绍兴市有关部门之邀为中华书局版《绍兴历史文化丛书·绍兴越窑》撰写《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等部分;又应上海社科院文学所之邀,为学林版《吴越文化的跨海东传与流布》撰写《吴越地区陶瓷文化在东亚的流布》等。这类研究还让我明白:一地的地域文化资料,往往从属于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文化范畴。如上林湖越窑,它的上位文化是越窑青瓷,再上一位是中国瓷器。我们的研究如果能放在更大的背景上进行,我们对该事物的认识就可能有质的飞跃。至少,我们的认识会水涨船高达到一定的专业水平。
二是开展当地名人研究,以推动乡贤精神遗产的继承发扬。我的研究分个体人物和群体人物两类。个体人物研究方面,出版了《吴锦堂研究》一书,为中国宁波和日本神户的吴锦堂纪念活动,提供了较丰富的学术资料,我的《吴锦堂对中国儒商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一文还被译成日文在日本神户发表。与此相关,还编印了《百年弦歌绕云天(上、下集)》以纪念锦堂学校成立一百周年,较全面地反映了锦堂教育精神。从在《中国江南——寻绎日本文化之源流》一书中发表《达蓬之路——徐福与慈溪达蓬山》开始,我又投身于徐福研究,先后出版了《达蓬之路》和《走近徐福》专题文集。另外还从海外移民的角度研究徐福,写成的《古代移民与徐福东渡》,作为《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的一章出版。关于个别人物的局部研究,则有《虞洽卿与中国商业社团》《虞洽卿对三北地区近代化的贡献》《试论古人眼中的虞世南》《谈谈高士奇的两本书》《袁枚与浙东食俗》等。从群体角度研究人物的,则有《慈溪商人在宁波帮中的突出地位》和《慈溪早期出国留学生的初步考察》等。
三是以新兴学科知识阐释地方特色,帮助人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地情。例如引入文化生态学的理念和方法写出的《三北历史文化的发展态势及其生态根据》《鄞州与慈溪:不同地理环境下的文化发展态势》;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研究徐福传说,写出的《一份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果戈理“建筑是世界的年鉴”的理念分析移民现象,写出了《对三北地区历代移民的考察》等等。由于角度新鲜、推理严密,有较好的社会效果。
四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接地气的本地资源,推动当地文明创建。譬如20世纪90年代讨论慈溪地域文化的特色,我以《在涛声浪影中成长的慈溪文化》为题向慈溪市委领导介绍了我的《寻绎慈溪文化之源流》一书中的有关论述,为讨论提供素材。后又发表《谈谈慈溪地域文明的主旋律》作进一步阐释。再如,为支持慈溪精神和当代慈溪人的价值观的讨论,我先后发表了《提炼慈溪精神,增强民性魅力》《慈溪民性的文化母体》和《重视民性弱点和失落点的总结》等文章;事后又撰写《当代慈溪人共同价值观解读》加以宣传,还承担主编《慈溪市市民手册》的任务以及支持编写中小学乡土教材、举办文化讲座等。
五是用文史记述或科普小品的体裁,介绍或补充地方志资料。这种写法,不回避因果说明和分析评论,也不回避使用文学语言,记述的历史演变及其深层意义就比较有可读性。例如《慈溪建县前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唐宋时期的越窑青瓷》《唐宋时期的三北盐业》《对三北地区移民的考察》《慈溪史事钩沉》《谈谈〈汉三老讳字忌日碑〉的文化史价值》等。有时甚至改成演讲稿进行宣讲。
六是利用全面掌握地情资料的优势,参与地方建设经验的总结提炼。我的《试析慈溪辉煌三十年的文化支撑》和《发挥地域文化优势 推动慈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等论文,以大量事实,论证了文化对社会、经济建设的强大推动、服务功能,呼吁大家关注地方的文化建设。上举的第一篇文章还在《新中国成立60 周年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宁波的实践研讨会》上获得论文特别奖。我另有《三北平原海涂开发的传统与创新》一文,总结了历代海涂开发的经验,在《全国海岸带和海涂管理与开发学术研讨会》交流后,也引起海洋研究专家对三北滩涂的关注。
由于个人的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我利用方志资源开展研究,为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服务的领域很狭窄,研究深度更不能令人满意,但这些点滴、浅薄的成果仍足以证明:从事地域文化研究是地方志工作者服务社会的很好的途径,千万不可失之交臂。
我已是一个85岁的老人,但我的“在求知道路上有所建树”的梦却至今未圆。想做的事实在太多太多。眼看精力日益衰疲,我只能对已有所积累的三项课题还存有实现的希望,想在无多的来日里加以完成,也恳望朋友们一如既往给予鼓励和帮助。它们是:
一是浙东三北地区文化生态的研究。在慈溪地域文化的研究中,我一直特别注意文化与其时空环境的关系,并提出过一些还不太成熟的看法。这与我所受的传统教育有关。在中华文化中,宇宙万物间都存在互相感应、相生相克的关系,从先秦时期的“天人合一”观到宋明时期的“万物一体”论,概不能外。后来学习了西方传入的文化生态学,我立即感觉到:这不就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应用吗?以后,我就经常将中、西相关观念混合在一起来考察“具有地域性差别的一些特别的文化特征及文化模式的来源”,不自觉地进行着所谓文化生态的考察。到近年,我在梳理我的地域文化研究成果时又发现浙东三北地区历史上的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形态的变化、经济产业的转移都有鲜明的特色,它们对文化发展的影响特别容易识别,是一个特别适合文化生态观察的难得窗口。于是产生了研究的冲动。目前,时空环境变迁的资料已收集得差不多,我将坚持努力,力争完成这个工作。
二是抗日烽火中的锦堂师范学校。1937年11月,日寇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不久杭州沦陷,锦堂师范学校亦于此年年底仓皇内迁至嵊县长乐,后随战事发展辗转于东阳、磐安、缙云,最终于日寇投降后的1946年1月下旬迁回慈溪观海卫东山头原址,历时8年余。锦堂师范在战火纷飞中坚持办学,规模不断扩大,教育质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不断提高,培养了大批乡村教师和抗战干部,谱写了一部振奋人心的捍卫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史诗,凝练成光辉的锦师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继承和发扬。锦师复名后,我与毕业于此时期的校友有极为亲密的交往,参与编辑了多种回忆文集,参加了十余次的校友聚会,和许多老校友促膝畅谈,所收集的相关史料实在应该整理出来留存于世,这是我的又一个心愿,但愿能够实现。
三是关于吴锦堂的研究。吴锦堂是我心目中最崇敬的慈溪乡贤,除已完成的关于吴锦堂的生平事业,关于锦堂学校的两本书之外,还有两件事也很想做一做。一是我手头的大量资料,须整理出来供后人参考;二是希望能写本《吴锦堂评传》,以纳入我近年的研究成果。但因为对吴锦堂生平中一些活动的评价,我还有不少疑问,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前,我的想法怕是难以实现了。
人生苦短,愿在无多的来日能继续在求知上努力,让我的“在求知上有所建树”的愿望得以最终实现。
2019年8月4日于秋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