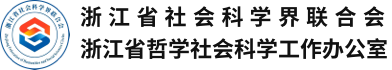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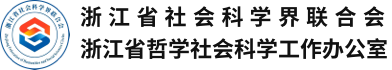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古至今,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恪守的坚定信念,也是我踏着先辈的足迹,引以自豪的自觉使命。
我叫冯志来,1936年4月30出生,义乌赤岸乔亭村人,父亲冯鹤毕业于浙江第一师范,曾任义乌、长兴、于潜等县教育局长,萧山、平湖等县督学。抗战胜利后,先赴杭州任佑圣观路小学民教部主任兼历史教师,后任金华师范民众教育馆馆长。父亲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把子女以来、匡、中、华四字为名,彰显他的救国情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以父亲为傲,激励我奋斗一生。
《半社会主义论》出台前后
1955年1月,我从金华农校畜牧兽医科毕业,被分配到浙江温州地区瑞安县政府农林科工作。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兴起,农村工作任务很重,大家除了本职工作外都要下乡,我们农林科的干部更不例外。县里办起了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后,我就被派到这个推广站工作,驻地在离县城十里的莘塍区。
莘塍区有10个乡,经济比较发达。农业以种植水稻、甘蔗和蕃薯为主。虽然人均耕地面积仅有几分,但农民们以渔业为副业,收入还是很不错的。当时有一个莘周初级社,收益分配二成按入社土地分,八成按劳力分,我记得每个劳动日可分得1.8元,而1955年我的月工资是30元,可见社员劳动收入比我高得多。其实,分红能象莘周社这样好的社是不多的,莘周社是区里的典型。但当时许多人认为,典型能搞好,面上也一定能搞好,只要典型搞好了,就可以全面铺开。
1955年7月31日,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批评了邓子恢等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全国农业合作社迅猛发展。记得1955年下半年的一个晚上,大约已是后半夜了,我在睡梦中被人喊醒,在县农林科科长的带领下,与莘塍区干部一起连夜下村,到那些不愿入社的富裕农民家里去抄粮食,要他们卖余粮。我们在一个担任过伪保长的单干户家里抄不出粮食,就把他的锅掀了,把人也抓了起来。抄粮食这一招可以说是强迫这部分农民入社的最高招式。我刚从学校毕业,总认为这些工农干部水平低,不执行“自愿互利”的政策。其实他们也很辛苦,若不给单干农民施点压力,他们的头上就会被戴上“右倾”的帽子。到了1957年,莘塍区已基本上是一乡一个高级社了。
由于农民入社并非都真正自愿,加上社内管理又跟不上,合作社内出现了“干活一窝蜂,社员磨洋工”等现象。所以,怎么办好合作社成了党委的大事,县委、区委、乡党总支,大家都在抓,我们农技推广中心站当然也不例外。大家白天搞技术工作,晚上就下村去开会。我们的副站长是国民党时期留用人员,解放后一直在县农场工作,有一套管理经验。我们一起下村,帮助合作社制订了一套管理办法,如“责任到队,定额到人”、“包工、包产、包成本”等等。但合作社不是农场,管理人员少,干部文化水平低,为其制订的这套管理办法难以操作。如挑粪,挑得距离有远近;除草,劳动质量有好坏。每天劳动结束,大家一窝蜂似地散掉了,一到晚上开会评分,就吵吵闹闹争执不下。所写的总结是纸上文章,好看担不管用。
1956年,我因出身问题被拉回机关参加肃反,实际上是陪斗。我虽14岁参加青年团,19岁参加工作,但因父亲曾在国民党政府中任过教育局长,虽然我家只有8亩地,并且父亲还有许多共产党朋友,如冯雪峰、宣中华、吴山民、童友三等等,但仍被划为地主。因为出身地主,我也难逃政治运动的折腾,所以,就被调回县里挨整。在机关接受批判的同时,我时断时续地被派到隆山高级社工作。在这段期间,虽然邻县永嘉在搞包产到户,瑞安的丽岙乡也曾出现过包产到户,但瑞安县控制得比较严,很快就进行了批判,致使包产到户没有蔓延开来。
1958年初,我被划分为右派,工资也从每月43元减为25元(实发12元),稍后,即被安置在瑞安郊区隆山畜牧场监督劳动,在隆山畜牧场,我经历了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大办钢铁运动,和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我清楚地看到“左”倾思想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对国家的前途,农民的命运深感忧虑。
1958年开始,国家建设搞“多快好省”,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生产搞“大跃进”,其狂热的程度,是后人所不可理解的。如瑞安近郊有一个遇溪水库,开始是按正规设计,动员了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工人、农民一起修筑的,大坝建设进度很快。但是,后来有一个省委常委来视察,认为大坝太宽,不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于是就更动设计,缩小了坝基,水库很快就建成了,但是,不久就被一场暴雨冲垮,淹了一个村子,洪水还冲到了城里。这个《浙江日报》曾予整版报道的水库就这样没了。
再如人民公社搞“一大二公”,实行的是供给制,常常要求大家“雨天当阴天,阴天当晴天”,“星星当月亮,月亮当太阳”,没日没夜地劳动,即所谓的“鼓足干劲”。实际上搞的是形式主义的一套。机关干部常常晚上被派去割稻,有些社员则晚上偷偷溜回去睡觉,大家消磨时间,不出力。稻子割倒在田里,没人脱粒没人收,甚至被洪水冲走。
又如“放卫星”,搞“大跃进”,隆山公社岭下大队就曾把15亩快成熟的稻子并丘成一亩,号称两万斤亩产试验田。虽然在“试验田”四周装上排风扇排风,上头有强灯光照明,但还是无济于事。15亩即将可以收割的稻子,通过稻田并丘,变成了一堆烂稻草,更严重的是浮夸风一刮,加重粮食征购任务。生产能力在下降,征购在增加,农民饿、病、流、荒现象越来越严重。
1961年下半年,我被摘掉右派帽子,送到以前浙南游击纵队的老根据地湖岭山区农技站工作。当时已允许开荒扩种,允许分自留地。群众开荒扩种,经营自留地的积极性很高,连我们农技站的5个人也向附近大队要了1亩多闲田,到一个中学去买来几担大粪,挑了好几里路,种了一丘油菜。
群众、干部开荒扩种和经营自留地的积极性,使我对合作化运动中过激、过“左”的做法从半信半疑走到了非常怀疑。于是,我就拼命地研读苏联的革命史,新经济政策及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茅盾论》、《实践论》和《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等文章,加上我在老区工作,接触了好多革命老人和贫下中农,我自信我思考的问题,是人民群众所想、所要求的,我觉得我已经悟到了一点真理。当时,我年轻又一无所有,无所顾忌,所以,就着手收集资料,于1962年初,写出那篇“臭名昭著”的《半社会主义论》。
在《半社会主义论》中,基于生产关系的变更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这一基本理论,我提出,我们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我们目前的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中国只有通过半社会主义的相当长的发展阶段,才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中国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社会主客观各方面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后,又趁热打铁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互助合作运动,这是十分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犯了主观主义、急速冒进的错误,从而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遭到了根本破坏。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便是在农村中实行属于社会主义范畴的“包产到户”……
1962年4月下旬,带着我的《半社会主义论》和铺盖,我回到瑞安县城,向农业局领导请假回家探亲。实际上,我是准备上京为农民请愿,并且也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已作了背水一战的心理准备。我把所有的家当都搬出机关,寄存在一个朋友——老兽医伍盘石家中。伍盘石是金华农校第一届毕业生,有一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怀,他一天到晚和农民打交道,是唯一真心实意支持我“为民请命”的人。而当时得知此事后,规劝我不要再去闯荡的是我们农业局的副局长戴福侠。他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为人正派,处世谨慎。他劝我接受戴右派帽子的教训,要考虑自己的前途。但讲到前途,我知道,在“左”倾路线统治下,无论我怎样安分守己,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我也只有挨整,当“运动员”的份。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只有人民的利益才是我的利益。何况我生于抗日战争前夜,父亲就名我“志来”,字我“铁肩”,望我将来能“匡扶中华”。出就是说,为了人民和国家,要肩担责任。所以,为人民为国家牺牲,本来就是父亲和我们这一代热血青年的心愿。我当时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感慨。
在上北京之前,我走访了瑞安城郊隆山公社原与我一起劳动过的农村基层干部,也到以前工作过的上望大队看望了一些农民朋友。我和他们讨论包产到户好不好,除了个别有“政治”头脑的人态度暧昧之外,大多数都从内心里想搞包产到户。而后,我又回了一趟老家。自1954年离开义乌县乔亭村老家,我已经七八年没有回去过了。这一次回去正是清明过后,看到的依然是满目苍凉。家乡的父老乡亲也都日子不好过,幸亏去年搞分田塍分自留地和开荒,种了蕃薯,才得以糊口救命。乔亭村当时有1400余人口,正常的死亡率为每年约十七八人,但1960年死亡人数却高达80人。我的一个堂叔冯永枚,就是因为日子混不下去了,吊死在村外一个凉亭里的。而令人感慨的是,这个凉亭内三面墙上都写着“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大跃进万岁”的大幅标语,中国走向何处?我们这一代人难道没有责任吗?到老家转了一圈之后,更坚定了我去北京上访的信念。
到北京后,我住在前门外一个老式的旅馆里,把我所写的《半社会主义论》分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晚上,公安人员来旅馆查房,问我来京办什么事,我拿出《半社会主义论》给他们看,他们看得很认真,浏览了大半本,结果不置可否地走了。
两天后,我接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的信,要我去信访室。接见我的是信访室的一位穿着旧呢制服的领导,他似乎心情很沉重地自始至终在看我的文章而不发一言。另一位穿军裤的则对我进行了盘问和批判,我和他吵了起来。后来《人民日报》刊出了戚本禹的《重新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对我在《半社会主义论》中所阐述的论点进行了批判。
我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种上访只不过是将文章送出去而已,能起什么作用呢?但我终于见到了信访部门的负责人,使中央机关知道有这回事了。我到北京的时间是在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几个月,中央正在总结经验教训,但我认为当时的纠错或纠“左”是有局限的,而我是从底层进行反思的,反映的情况和当时的实际比较接近。
从北京回来的火车上,我听到安徽分责任田,老百姓很快填饱肚子的传闻,心里很快活。但是回到浙江不久,就听说安徽也在纠正包产到户了,心里很气愤,于是就又写了第二篇文章——《怎么办》。文章的主要观点是:目前的困难主要是由于“左”倾错误造成的,它始于1955年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至今尚未终止,所以有必要加以清理。不顾客观条件地加快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否定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基本原理,过分地强调了人的主观愿望与上层建筑的作用,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大跃进”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高速度的口号下,破坏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以致出现了一种与愿望适得其反的结果,造成了空前的经济困难,使共产主义(包括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受到歪曲和庸俗化。由于否定了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适应的普遍真理,否定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长期性、缓慢性和不平衡性,因此,农村中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不能不继续尖锐地发展。文章主张:在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里,对于那些集体经营条件已经成熟的地区,应全力巩固和发展集体经营,而集体经营条件还没有成熟的地区,应当在现有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对于少数赤贫户,可根据他们自愿,在国家扶持下实行集体经营。
《怎么办》一文,我是以冯雪峰侄儿的身份寄出的。因为一则雪峰已经打倒,我想是否给他增加麻烦也已不很重要了;二则这样可以引起上面的重视,促使决策层能看到这篇文章。
1962年是痛苦的一年,这一年从上到下都在回顾和总结合作化以来所经历的种种沉重的教训,形势迫使党中央领导层开了七千人大会,不得不对一些“左”的政策进行一些调整。但犯错误的同志却不愿彻底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教训,仍要坚持“三面红旗”。理论上,“左”倾的东西仍很有市场,形势还是很严峻的。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又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反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当然,我还是清醒的。两篇文章出去后,我这个摘帽右派在机关里是无论如何也待不下去的,与其在机关等死,不如一走了之,其时正逢机关干部大批下放农村当农民。我就申请下放回义乌。但我这号人连下放也不容易,幸亏县农业局的领导还有一点同情心,批准了我的要求,这样,我总还算是“下放干部”,我带着几十斤重的一箱书(因别无他物),于1962年8月回到了一无所有的“地主”老家。家里除了土改时留下的一间楼房外,几乎连只碗都找不到,我怎样生活下去真成了个大问题。我从农村出去,又回到了农村,见到的都是公社贫苦的社员,他们待我都很好,但都是穷乡亲,谁也帮不了我。我家几代都是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知识分子,现在,我连自己也落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话说?
我在家乡混了一段时间,在这几个月中,我走江湖卖苍蝇药,挑着爆米花机去江西、湖南爆米花,但这些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随时随地都可被阻止和干预。4个月后,“阶级斗争”又找上门来了,大概是省委贯彻八届十中全会决议,要清算“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而我正是少有的代表人物。
记得那一天,我因爆米花机给湖南郴州管理部门抄走而回到家里,不料逢瑞安县公安局和农业局各派一名股长来请我回去辩论。其实,他们已带来了手铐,并到公社办了逮捕手续,如我拒绝,他们就要把我抓回瑞安。我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所以也无所畏惧。他们中有一人还是我的老同事,我请他们吃了饭之后,就和他们一起回到了瑞安。
这时我才听说:我的文章先在温州市委党校受到了批判,因文章没有署名,起初还以为中央什么领导犯了错误,后来才知道是我这个小干部写的,又感到好奇。但他们心里还是很紧张的,我的文章被批判后,即被收回并加以焚毁。听说省委也在一个全省干部会上对此加以批判,毛主席还称我们这些主张包产到户的人为“浙江的单干理论家”。
我被隔离在农业局宿舍。县委专门成立了一个批判小组。他们先拿来一份《半社会主义论》的打印稿,上面有温州地委第一书记张一樵的:“打(印后)发(给)常委”四字,问我这份材料是否是我写的,并叫我也签字。接着共开了三次批判会。一次是小规模的,共十余人。会上,他们还追问我到过哪些农村放“毒”,宣传包产到户,这一点我一概否认;其次,他们要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我是“老运动员”,我知道若不承认,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老是磨时间,一点意思也没有,所以,我就说:“你们批判的我都承认”,并照他们的要求进行了检讨。这样,他们算应付过去了。于是,就开了第二个会——全县科局长会议,对我加以批判。这是全县开展批判的预演。预演结束之后,就开了全体机关干部大会,对我进行批判,然后再叫我等待处理。
在此期间,我住在农业局,他们发给我6元 的饭菜票,行动也可以自由,只是没有钱花。1963年春节后,我被安置在飞云江农场劳动。1963年5月,省委下了文件,我又“重戴(右派)帽子”,由一个警察遣送回原籍义乌县,接受监督劳动。
在老家,老百姓似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所以,对我几乎没有什么“监督”。同年10月,我还结了婚。1966年,本村“大四清”开始,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又失去了自由,成了“牛鬼蛇神”。但不久,我发挥所学兽医专业的优势,给农民们医猪、医牛,受到群众的保护。加上我身强力壮能够劳动,所以一家子马马虎虎挺了过来。
1979年右派摘帽改正后,我又回到瑞安县农业局工作。在右派改正过程中,感谢瑞安县农委周士昧主任派人去省档案馆抄回了《半社会主义论》和《怎么办》两篇文章。1980年,我再次将文章寄给中央,虽然没有答复,但我在报上看到有提半社会主义理论的,也有人提初级阶段理论,心里很感快慰。
《兴市边鼓集》:义乌发展的实践与思辨
我在青年时期,凭着满腔热血,写过几篇文章,出发点是为人民说真话。但是在狂热的年代,真话是不好说的,说了就要遭殃。我遭殃以后,无声无息过了二十余年。
1981年,我调回义乌工作,1987年12月,还当选为省七届人大代表,后来又被安排担任了县(市)政协的副主席。
1988年,我担任了义乌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还是不想写什么大作,只是在其位要谋其政,而且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扣帽子、穿小鞋的事也不那么有市场了,真话可以讲了,也比较有人听了,加上我们的书记、市长都很开明,所以,从工作需要出发,就断断续续写了《义乌经济发展战略思考》《义乌市实行兴商战略的回顾和展望》《小商品市场应冲出国界》《应该加快培育人才市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继续培育完善市场体系 推进“兴商”战略的实施》《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义乌实行兴商建市战略的实践和几点思考》等文章,目的都是想对义乌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出一些主意,讲一点理由。虽登不了大雅之堂,却是对义乌人民和党政领导尽一点责任。
我写这些东西比较粗糙,有的比较简单,随感而发,大都是为了解决义乌的一些问题,或是总结义乌改革的一些方面,并且有一部分没有付诸实施,但侧重点是为义乌发展培育市场,也就是为“兴商建市”战略宣传、辩护。当时看来有点“离经叛道”,内心多少也有点压力。自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我的这种担忧,也不存在了。但是风雨总还会有的,只是风雨过去了,就是明媚的阳光,而且风雨经得多了,也习以为常了。路还要照样走下去,这就是我的人生哲学。
义乌地处浙中,浙赣铁路横穿县境,杭温公路和衢、宁(甬)路在境内交叉。自秦赢政廿五年(公元前222年)建县至今有二千余年历史,但长期停留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矿产资源贫乏,棉、麻、茧等纺织原料紧缺,离大城市较远,国家无大中型项目投资,工商业不发达。1979年义乌街头出现一些经营小商品的摊贩,1982年政府通过调查,冲破“左”的思想禁锢,保护和支持农民进城经商,正式开放小商品市场并提出兴商建县的发展战略,到1987年为止工农业总产值已增长3.14倍,工业产值增长5.1倍,农业产值增长1.54倍,地方财政增长2.55倍,城乡年末储蓄额增长4.96倍,上述五项指标,增长速度非但每项皆超过金华全市,而且也超过兰溪和东阳。
1988年,义乌撤县建市后,以后怎么办?我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总结历史的经验和义乌的实际,证明义乌兴商建县的路子走得对。兴商建市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义乌市场的发育,不仅发展了商品市场,还积极地开辟生产资料市场、金融市场、文化市场、房地产市场、农贸综合市场、人才劳务市场。兴商建县的过程,也推进了各项改革。首先,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参与市场竞争,促使国营、合作商业加快改革步伐,利用其优势,改变经营方向,瞄准小商品市场,扩大原材料批发业务,既帮助了个体工商业户,又提高了自己的经济效益。其次,有些农民把商业资本逐渐转为工业资本,实行工贸结合的经营方式,冲击了农民、集体工业,出现争人才、争技术、争原料的现象,迫使国营、集体企业非改革不可。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瞄准市场,发挥大厂的骨干作用,才能摆脱困境,继续发展。第三,农民成为商品生产经营者,很快地富起来,出现物价的波动,以及多种市场的兴起,推动对“端铁饭碗”的干部和职工的劳动制度的改革,为平等竞争,开拓人才、劳务市场创造条件。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义乌的经济战略,当时我又提出初步的设想:以贸易为导向,以商兴市,紧靠东南沿海口岸,发展与温、台、丽的紧密合作,向腹地的大、中、小城市辐射,逐步建立起贸工农一体化,上规模、全开放的经济格局,把义乌建设成为繁荣、富庶、文明、整洁、安定的中等城市。
为继续推进兴商战略,实现以上战略目标,建议首先要以大社会、小政府为目标来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工作应“运筹帷幄”,增强宏观调控职能,减少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职能。不能把政府领导降到经理厂长的水平,忙于日常琐事之中。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要切实创造条件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正在继续扩建,生产资料市场要抓紧建设和开张,同时还要继续完善和开拓金融、人才、劳务、文化、技术、房地产和特需商品等市场。第三,要完善和发展贸工农一体化的生产服务体系,转变经营管理机构和行政性公司的职能。第四,要继续下力气搞好以稠城为重点的城镇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力争开通民航和程序控制电话。
义乌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可以说是一个创新之举。
义乌在“兴商建市”战略方针指导下,商品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推动了城市的建设,以往城市国有土地是无偿、无限期使用的,房地产开发也很混乱,房地产市场没有很好管理。1988年,朝阳门改造工程和站前高架桥附属商品房拍卖的尝试,为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城区开发和建设积累了经验,也表明实行城市土地有偿使用是可行的。所以,义乌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就应运而生。1990年11月,在市长直接领导下,由市经济研究中心和体改办成立研究小组进行筹备。1991年4月份,我们呈交政协讨论反复协商,并提请人大讨论;5月份,由市府报请省政府要求批准试点;7月下旬,建设用地已统一实行有偿有期出让。截至1992年1月25日止,全市已出让使用权的国有土地面积为17135.96平方米,总共可收取出让金5596.4万元,平均地价为每平方米3256.96元。这笔出让金总额相当于义乌市1990年全年收取的城市建设维护费的24倍,超过了义乌市1990年兴建的六大工程(民航义乌场站、仓后立交桥、城中路五叉路口、稠州中路、绣湖西路、仓后路)的总投资,使义乌市城市建设走上“投入――回收――再投入”的良性循环轨道。
义乌市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基本做法:
首先提出了“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地产起步,房产随后;城镇试点,农村控制;积极稳妥,依法进行”的改革思路。然后成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计划、体改、城建、土管、财税、物价、建设银行和房地产管理等部门的领导组成,市长任组长,分管城建、土管的副市长分别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国土办),负责日常工作。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涉及面广,社会震动大,改革的顺利进行需要广大干部群众统一思想、更新观念、深化认识。我们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简报、宣传窗等各种宣传工具,采取召开动员大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举办宣传周、培训班和咨询服务等形式,广泛深入地宣传改革的必要性、内容、具体做法和方针政策,取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
其次,改革强调依法进行,重视政策制订。已出台的有《义乌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试行办法》、《义乌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试行办法》、《义乌市受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若干优惠政策的暂行规定》。即将出台的有:关于职工集资建房、城市规划区内土地征用等具体规定。
第三,设置了相应的机构,理顺了关系。为了对城镇国有土地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征地、有偿有期使用的需要,市里专门设立了地产管理所。其主要职责是:负责城市规划建设区内的统一征地、出让和地籍管理、土地登记发证等工作。为了形成统一的房地产交易市场,市里又专门设立了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所。其职责是:按国家有关房地产价格评估原则和标准,对交易的房地产进行勘测、丈量、价格评估;依法办理房产登记、变更登记、鉴证及权属转移等手续,换发《房屋所有权证》;依法查处非法交易活动,制止场外交易,监督、检查房地产经营单位的交易活动。
最后是精心组织实施。1991年8月5日,义乌首次进行国有土地使用权投标会,以站前小区3号楼坐落土地使用权向社会公开招标作为改革的突破口。该地段处于火车新客站前,客流量大,是寸土寸金的宝地,市场容量大,容易分割。一部分用投标方式出让给个体经商户,另一部分用协议方式出让给市房管处。保证了首次出让的顺利成功。
义乌市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作为浙江省政府的试点,意义深远,为全省改革工作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浙中史话》:地域文化探索
义乌以小商品市场闻名于世,而山水名胜更是目不暇接,惟少为人知。
中国佛教史上有传的2000多位高僧中,号称“大士”的中国人为数极少,傅翕就是其中之一。宋朝以后被列为五百罗汉之列,称为善慧尊者。傅翕是南朝东阳郡乌伤县稽亭里即今浙江省义乌市人,生于齐建武四年(497年)五月初八,号称双林善慧大士,认为是弥勒应身,代释迦坐道场。正如续高僧传中所述:“双林大士者,体权应道,蹑嗣维摩,时或分身济度为任,依止双林,导化法俗;或金色表于胸臆,异香流于掌内;或见身长丈余,臂过于膝,脚长二尺,指长六寸,两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所以傳大士受到四方信徒的崇仰尊敬,也受到梁武帝的重视,延请他进京说法讲经。至今义乌市图书馆尚藏有《傅大士文集》一部,有详细记载。傅大士依松山双梼树结庵修行,梁朝普通元年结庵建寺。该寺名噪一时,隋文帝曾三次派特史持他的亲笔信前去慰问该寺住持——傅大士的门徒惠则法师。这个寺北宋时尚有僧舍1200间。南宋被皇帝定为五山十刹之一。明朝重修双林寺序中称:“乌伤上游,古刹双林,在震旦国中,称庄严第一。”至今该寺尚存五代铁塔一座,为中国古代铁塔之稀珍。双林寺在历史上名声显赫,也证明了傅大士在中国佛教中的地位,而且日本的佛教信徒目前还非常敬重傅大士。
傅大士是中国人,为什么能成为佛教菩萨?同时梁武帝信奉佛教,在京城里,自国师智者法师以下道德高僧数量非常可观。只有傅大士,年非长老,也不是和尚,到京师之后,“京洛名僧,学徒云聚”,王侯公卿连皇帝也向他“问慧咨禅”,这事谈何容易!诚然,傅大士是“绝世通人”,所以皇帝故加“殊礼”。但是傅大士原本是一个为人作佣的农民,又没有读过书,为什么能“穷尽太虚”、“普应万机”呢?清朝学者朱一新说:“惟大士生自西天,证越十地,法相不动,妙香自闻。开达摩东渡之先声,修祇夜南翻之正觉。从此甘露降树,黄云覆山,门任槌开,经随轮转,救众生苦,兜率迟归,继七佛踪,释迦早引。”原来佛教认为他是一个天外来的佛。佛与现代外星人概念,究竟有无联系,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因为宗教与迷信固然有不解之缘,但宗教与科学似乎也有联系。这就很少被人所知和理解。最近发现佛教关于宇宙年龄的记载,竟接近于科学测定。关于宇宙理论,科学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到现代才走到大宇宙理论上来。但佛教的宇宙观早已和这个理论相吻合。所以佛教当中必然有一些超前的科学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限于人类的知识水平,很难理解,变成一些扭曲了的神话。所以关于傅大士的种种记载,应该说是有一定依据的。
傅大士24岁,时间是梁普通元年即公元520年,在稽亭塘下,遇一梵僧嵩头陀。嵩头陀说:“我和你都是第四天兜率宫来到世上救人,你什么时候回去?”大士瞪目结舌。嵩头陀说:“你忘了,请到水边来照照影子。”一照,看见圆光宝盖,便悟前因。嵩头陀还指点他在双梼树下结庵修行,白天佣作种植,夜里敷演佛法,这样苦苦修行,过了七年。一日,忽见释迦、金粟、定光三佛来自东方,放光如日,复见金色,自天而下,集大士身上。从此以后,他的身上常出妙香。空中每闻唱言:“成道之日,当代释迦坐道场。”引得四面八方的群众,成群结队来“问讯作礼。”郡守王哮发现,认为是妖妄,就把他关起来,关了十来天:他不饮不食,也没什么,大家都很惊奇,郡守也就把他释放还山。这样名气就更大了,佛法愈精进,门徒愈多,每日钟鸣,有仙人自空而下,随喜行道。大士得到了首楞严三昧。而此三昧唯十地菩萨方能得之。自此佛徒都知道他是十地菩萨示迹,弥勒应身。自号双梼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
大士成道以后,以“现天心、资善会,度群生”为任,出示种种灵异。有一次他去接度他的叔祖父傅孚,在此过程中。曾拨开前胸,出示金色天香,并使“孚”梦见大士,翔空破壁。他的叔祖父从此稽首愿为弟子。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534),傅大士应诏到京都见皇帝。同年闰十二月八日晨第一次请他进宫。皇帝事先闻大士神异,叫人预先将所有宫门上锁。傅大士预先感知,做了一双大木槌,仅扣一门,所有的门便全打开。见了皇帝也不礼拜,经自在宝榻上坐了下来。皇帝问他:“你的师父是谁?”他说:“从无所从,师无所师。”吃了饭他就跑了出来。
有一年,信安僧朔等人寻上门来,不想行礼,但一看傅大士,身升丈余,这些人惊惭不已,马上争先礼拜,拜后才看到傅大士的本来容貌,并求为弟子。又有会法师,来试大士的佛法,带了80余人来索食。他家里只有4个人吃的饭,他分别给80人吃,这些人吃了都感到吃得很饱。
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四月二十三日,傅大士告诉他的儿子普建、普成说:“我从第四天来,是为了普渡众生。”至二十四日,大士圆寂,年七十三岁,肉色不变,七日乌伤县令陈锺耆来结香火缘,取香火次弟相传,传至傅大士,大士犹能反手接香。
以上神异,多系众目所见,当然不免有神化了的东西,但当时所记,不至于毫无依据。现在看来好像是一次外星人与地球人接触事件,如见释迦等三佛时其光如日,不正是现代所说的“飞碟”吗?又如圆光宝盖,不正是现代太空人的装束吗?另如每日鸣钟有“空界神仙,共来行道”的记载,应有众多信徒所见,不会毫无根椐。这些“仙人”,不正是目前所传太空人,又能作何解释?何况,当时的郡守王哮,把他视为妖妄。后来皇帝亲自试他,所谓“槌任门开”事件,但恰恰证实了他的“神异”。何况他一个农民,能“自通墳典”,要“说偈论经”,做到“滴海未尽其书”,“悬河不穷其义”,如果没有科学的东西帮助,在乡下怎么做得到呢?这个答案据傅大士文集传录载:“我(傅大士)学道初始,见一佛身长丈六,放金色光,从天上来,东面而下,其光赫赩,遍虚空中作黄金色,都不见有屋,如生虚空。”可见他是受“佛点化”,或本人就是佛所应身。另据义乌旧县志记载:“傅大士死后,远近人们络绎登山行道,塔上燃灯供佛,声唱佛名,但见四面神灯布列塔下,或出现在空中,大如车轮,人谓天灯。”这天灯和现代的不明飞行物“飞碟”又何其相似!“佛”究竟是否现代所谓外星人,那有待于用科学态度进一步地研究。
1993年5月12日,世界科技译报载:美国总统克林顿接任以来,白宫上空出现一片奇怪的云,先被警犬察觉,经情报局用最先进的仪器探测,发现白宫内藏有许多类似激光发射器,电波直接发射到白宫上面那团持久不散的云。所以这片云被认定是外星人监视白宫的装置。联系到我们古代双林寺松山因黄云覆盖三日不散的记载,故名云黄山,难道这和现代的白宫事件不无关联吗?
傅大士经历齐、梁、陈三朝,受到梁、陈两朝皇帝的重视,双林寺住持还受到隋文帝隋炀帝数次亲自写信慰问,这些都有确凿的史料可证。傅大士碑文由南朝陈仆射徐陵所撰,收《徐孝穆集》,词源许多条目都是提到双林寺傅大士,可见所载不虚。
傅大士现象,组成义乌古代灿烂文化重要的一页。我虽不是佛教徒,采写《傅大士传》,最起码,可增加对1500年前佛教发展时期的了解,增加人们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增加一点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有益于新文化的发展。
还有,我幼年听父辈说,老家桥亭村,并非一座桥一个亭,桥是古人的姓,亭是古代的行政单位。长大以后被打成右派,遣返原藉,监督劳动。在家就研究起故乡的历史来了。收集了一些传说,悟出了一系列地名和历史的关系,终于在1991年《江南游报》上,发表了《三国大小二乔出处考》。以后又不断有所补充,写了《东吴皇川胜迹探微》发表于1993年《浙江地名通讯》第3期和1995年《中国文物报》,20来年过去,几乎得到省内外的认同,但是近年各地掀起发展旅游和争夺名人的热浪,二乔故里之争就在全国展开。二乔是哪里人?古人没有留下片言只语,只能从传说、地名和历史背景加以归纳分析推理。我对破解千古之谜——二乔之诞生地是很自信的,二乔故里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浙江省义乌市赤岸镇。而其它地方也抢二乔故里的理由,无非三条:
一、认为二乔的父亲——乔公即乔玄,所在只要和乔玄有关的,都认为是“二乔故里”,但是乔玄比曹操年纪还大,孙策攻破皖城时已死去多年,所以把乔玄出生地、结婚地、居住地作为“二乔故里”都是伪证。
二、潜山县有“松竹二乔宅”之说,是二乔结婚居住过的地方,但不是出生地,明初“吴中四杰”徐贲有“乔公虽在乱离中”之句,阐述乔公携二乔流离而来到了皖城,黄山谷所谓“松竹二乔宅”本是这个意思。
三是有小乔墓的地方,这是小乔归宿地,更不可能是“二乔故里”。
“二乔故里”归属,应该说不难判断,尤其从三国东吴历史大背景来看,“二乔”不过是三国惟一的女政治家——吴夫人,用美女(可能是其亲戚)二乔,一嫁其子孙策,一嫁大将周瑜,以笼络周瑜巩固孙周军事集团的一着妙棋而已。我将破解“二乔故里”之谜的一些短文,用史学界惯用的一系列地名和传说等作证,加以结集出版《二乔故里解谜》,以飨同好,并寻求对此问题之研究不断深化。
义乌一掌之地,捏紧了就是拳头,故素有拳头文化之谓。而绍兴却有师爷文化之传统。拳头加师爷或者说实力加智慧,就是於(乌)越之文化。古可称霸中原,今能走向世界。所以,我认为於越文化很有研究价值。
要研究乌越文化,首先要弄清文化产生的源头和地域。否则,一切皆无从谈起。但是这个源头,经历了秦始皇的摧残已被遗忘或扭曲,要还其历史真面目,还是很不容易的。
我有缘对此作了一些研究。那是20多年前,金华市民政局一位地名专家问我:“义乌吴店有一座子城庙,这个子城究竟是哪一朝?哪一代?什么样的子城?”我虽然曾经是《义乌县志》的编辑,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却引起了我的兴趣,以后我下决心读古藉,如《山海经》、《越绝书》、《吴越春秋》等等,并结合野外调查,利用本地人熟悉本地的情况和懂本地语言的优势,从地名、土话等方面切入,1999年开始在《上海师大学报》发表了“虖勺水·於(乌)越城·义乌市”。此后又写了《山海经与浙江古地理》、《成山、句无和故越都浅析》、直到2004年对被遗忘了的历史,已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写了《於(乌)越古史考辨》登在政协义乌市文史资料上面,这几篇著作主要说明古乌越活动的地理位置,至今又10余年过去,感觉以前的认识尚有所欠缺。比如史书提到的,句无亭在哪里呢?是否就是句无故国?所以又写了《义亭镇勾无亭和越王城》,现一并结集《乌越古国探源》,付诸探讨和指教。
乡土文化是一切文化之母,是思想者的精神家园、文化之根。爱恋乡土,进而爱恋祖国,原本就是人类共同的情怀。中国人对乡土的怀恋,就像树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义乌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有着丰厚的人文历史,由于史前文化的记载少知甚少,现在发掘出的恐龙文化、上山文化等遗址,为义乌增添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根据地名走访竟然发现这里是羲和文明古国的发祥地。
路漫漫兮,吾将上下而求索。